人生就是一本書——悼念李強老師
李餌金
(beat365社會學系2000年入學的碩士。現任北京賽諾營銷顧問公司、北京及客科技有限公司董事長)
前些天,突然在“強學會”微信群裡看到同門師兄的接龍,知道李老師去世的消息,不敢相信也不願相信,心情很沉重。
參加李老師的遺體告别儀式的那天,聽見肖林兄說:李老師還有一篇遺稿要在《社會學研究》上發表。當時,李老師還親自在網站操作投稿,打電話問肖林,如何解決網頁操作時遇到的一個技術問題。
一時,複雜的思緒湧上心頭,人生的一件幸事是:人走了,字還在!
它們将被廣泛閱讀、轉載和引用,幫助這片土地上的人們凝聚共識,個體的生命似乎以這樣的形式可以得以延續。從這個意義上來說,李老師并沒有離開。這樣想了想,我的心情也輕松了不少。
李老師筆耕不辍,通過文章啟發着無數人。微信朋友圈裡,有人看到李老師去世的訃告,留言道:“文獻中崇拜的學者!”
而我與李老師接觸的點點滴滴,跟過電影一樣,一幕一幕浮現眼前。受同門師兄師姐們的衆多生動的紀念文字的激勵,我感覺也應該将與李老師相處的片段寫成文字、分享出來,這才是對他的更有意義的紀念吧!
一、書
1996年11月,我還在上大一。有一次去北京圖書音像城找書看,有一本黑色的書一下子抓住了我的眼球,書名是:當代中國社會分層與流動。

翻了翻目錄,發現這内容也太解饞了!階級、階層、貧富分化和如何流動到上層,這些話題是如此的重要,跟命運的關聯是如此密切!趕緊買了下來。回學校宿舍,幾乎是一口氣讀完的。這些問題極其複雜不容易講清楚,但是,作者卻能用淺顯易懂的語言講得清清楚楚,甘之如饴而且好消化啊!
對于我這個上大學之前根本就沒有走出過丹東市的山溝土小子而言,這本書簡直就是突然身處北京正在好奇打量這個花花世界時的開天眼之書。
那裡有很多實實在在的統計數據作為支撐,還把我們天天背誦的馬克思主義理論從一個新的視角做了解讀,這太有趣了!而且,裡面還有很多故事案例,比如因為恢複高考,有人通過上大學改變階層;有人通過“賣茶葉蛋”,收入超過了“做導彈”的科學家,社會出現了腦體倒挂的現象等等。這比看小說、傳記之類的文藝作品更靠譜、更貼近社會實際,甚至,文字也更有意思!
這是我上大學期間買的第一本課外書。後來的日子裡,它一直跟着我。沒想到,這是一段緣分的開啟。那本書是1993年出版的,作者正是李強教授。我記得那本書有李老師的頭像,很精神。看書的時候,就仿佛聽他親口講述一樣,若有神交。

四年之後,也就是2000年,大學畢業考研究生,有調劑的機會,一個選擇是政治學系,另一個是去社會學系。我毫不猶豫選了社會學系,成為複系後第一屆碩士生。甚至,有幸選到李老師作為導師。這樣與李老師有了近距離接觸的機會。
有一次,我被指派到李老師家取一封重要的信。後來知道,好像是博士入學考試的專業題。那個時候也沒有快遞、閃送之類的,需要派靠譜的人去取送。
當時,他還沒有搬到清華,仍居住在中國人民大學校園裡的寓所裡。我需要等着他在裡屋寫東西才能拿走那個信封。我等待的時候,他囑咐我說:屋裡有書和雜志,可以看哈!
屋裡這好多書,可見一斑他對書的熱愛。後來,看李老師的回憶文章中,他說在北大荒的9年,想盡一切方法找書看。這種對書的熱愛、對知識的渴望、對真理的渴求,對我有很大的影響。我現在家裡也是滿滿幾排書架,看多看少先不論,至少“氛圍感”先給拉滿了。
李老師曾說,之前自己有一本書稿,是手寫的,投給出版社,居然被出版社給弄丢了!當時,聽他講這個故事,我心裡還怪着急的!隔着時空給他出主意:提前複印一下呗!他回應了為什麼沒有複印備份的原因,怎麼說的我給忘了。隻是覺得,嘔心瀝血寫就的書稿就這樣丢了,真是太可惜了!要是早點有電腦就好了!
李老師寫字很認真。他有一個本子,是通訊錄。第一次看他打開了這個本子,我就驚呆了!這得多細心嚴謹的人,才會有這麼工整的手寫通訊錄啊!上面密密麻麻的是人的名字、電話号、BP機号、郵政地址等信息,一筆一劃的整整齊齊。甚至,還做了拼音索引标簽,方便翻頁查找。
後來我也曾經照着他的那個本子的樣子,買過類似的,厚厚的,也一筆一劃記錄過。不過,沒有多長時間,所有通訊錄就都變成電子版的了,那個本子就沒啥用了。但是,那種嚴謹的作風,卻難以忘懷,潛移默化影響着我做每一件事情的态度。
寫畢業論文那年,我需要使用Andrew Walder的“新傳統”的原書。但是,查了幾個圖書館,也找不到。跟李老師說了,沒想到,他那裡就有這本書。于是,他把書借給我,論文的理論脈絡得以豐滿充盈。
那本書裝幀很好,但是被揉的有點軟了。一看就知道李老師是翻看了很多次,不少頁面做了輕輕的标記。看書時,我腦補了李老師正在看那本書時的狀态,不由自主看得更加認真了。
畢業之後、創業之前,我在國際勞工局(ILO)工作一年多。有一次,李老師給我打電話,問我能不能找到一本國際職業分類的書,這本書在别的地方找不到。我一查,果然ILO北京局的圖書室裡有這本書。很高興自己能幫上李老師這個忙。于是,一個下雪天,我拿着這本書,跟他一起到照瀾院複印相關的頁面,邊走邊聊。
在某篇文章中,李老師說感謝李铒金幫忙找了資料。我很意外,這一點點小事,居然也可以變成文字進入嚴謹的文章中!内心溫暖的同時,也感受到文字的巨大力量。後來,我看有同學發的李老師的書架照片中,有一本複印資料上面寫着我的名字,應該就是這個資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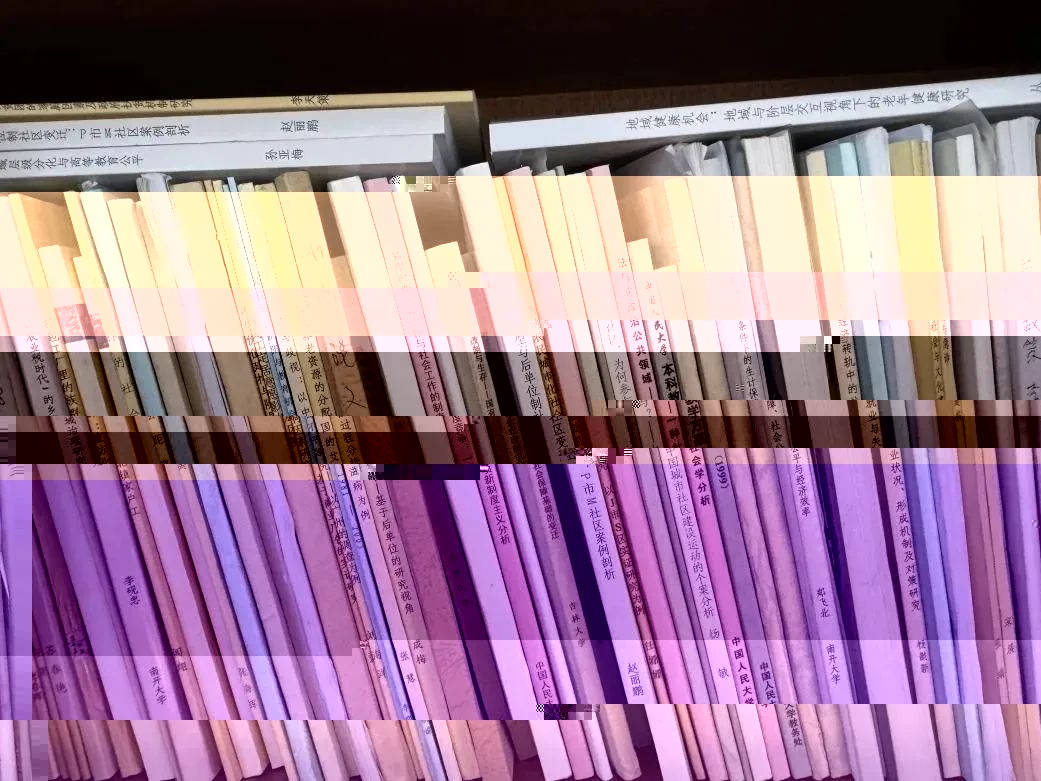
二、田野
念書的時候,很幸運參與了李老師所主持的一些研究項目。
當時陶傳進老師、李斌老師讀博士,我跟着他們,先後到了北京市西羅園社區、方莊社區進行入戶調研。還去了甘肅武威、河南焦作、山東東營等地采訪農民、工廠管理人員等。這樣的機會很寶貴,讓我得以與衆多不同身份的人交談,看到多種多樣的人生橫截面。
這對我産生了很大的影響。後來我的創業項目,就是跟調研有關的,屬于市場調查行業,也算是從李老師這裡得到的啟蒙,至今已經有19年時間了。
李老師曾經提出的“心理二重區域”的概念。同樣一件事,跟生人說時是一個說法,跟熟人說可能就是另外一個說法了。這簡潔的概念,一語點破了常規問卷調研中可能遇到的局限。要真正了解社會,也必須在相對長期的互動過程中去觀照。
李老師後來曾經樂觀的說,自己在黑龍江下鄉的9年時間裡,其實是做參與式觀察。他詳細的描述自己蓋房子的技巧和過程、到處找書讀的經曆等等。他還把騎馬飒爽照片,作為微信頭像,讓人印象深刻。
那是正念當下的好榜樣。也讓我讀到:人生就是一場體驗,心所安處,皆可見真理啊!

三、身教
有一次,李強老師邀請日本著名數理社會學家高坂教授做課堂講座,他以數理統計的方法,分析日本社會的分層情況。講座過程中,高坂教授總是提一個詞:real estate。這個詞出現的頻率很高,而且在表格中,這項所占的比例很大,感覺是個很關鍵的因素。
當時我不太理解那到底是指啥。手上也沒有詞典,當時的手機也沒有查字典的功能。當時中國的房地産業還沒有如火如荼,我們對這個因素會影響社會分層也還沒有切膚之痛。
正好李老師坐在我前面一排的位置,我就厚着臉皮,探着身子湊到他耳邊,捅了捅他的肩膀,輕聲問道:他是說房地産吧?
李老師輕輕點點頭說:對。
後來很多年,我都記得這個情節。一是覺得自己這麼簡單的詞都不認識,太丢人了。二是覺得自己在課堂上這樣私下捅咕老師問問題,好像很不禮貌。
但是,李老師沒有瞧不起我、批評我,對我還是那麼和藹的态度,讓我印象很深刻。
身教勝過言傳。很多時候,當我面臨同事,準備發火或者已經發火的過程中,總會在腦海中浮現起與李老師互動的這個鏡頭。提醒自己,要耐心、耐心再耐心,給成長一點時間。
有一次課堂論文,我寫了一個關于農民工是城市的邊緣人的文章,自鳴得意,還跟同學吹噓自己寫得多麼多麼牛掰。沒想到,李老師手寫的意見,一下子就戳到了論證中存在的緻命問題,清晰而明确,盡管沒有批評的意思,卻讓我一下子認識到不足之處、如夢初醒。他的字寫得也是十分工整,仿佛一封信,開頭是:铒金,這篇文章的标題是…
這些年來,沒有聽說過李老師高聲批判過任何人,總是謙和的态度對待所有人。
多次聽張華師母說:李老師在家裡也從來沒說人的短處,都是在說人長處。
有一次與李老師交流,佳燕老師也在。當時,我總是直呼“劉佳燕”這個名字,潛意識裡認為她比我年齡小幾歲,而且入門時間比我晚,直呼其名就好。李老師卻柔和的提醒我,讓我叫她“佳燕老師”。我瞬間意識到自己的問題,趕緊改口。
年齡越大的時候,越感覺這其中蘊藏着深厚的人生智慧:把“我”放低放小,把所有人都當老師看,人生的路才會越走越寬。何況人家已經是博士後,學識遠在我之上,更應該敬心誠意叫聲老師才對。
其實,在生活中,我與李老師說話并不多。有的時候,甚至不知道該跟他聊些什麼。畢業之後,跟系裡另外一位德高望重的老師交流,發現他居然也有同感。這讓我很驚訝:他們是同事關系,不是師生關系,怎麼也會除了工作就不知道聊些什麼呢?
可能是因為他極度專注,除了工作時間,其餘時間都在工作,有時不我待的意思。
最近,還有一句話總是萦繞在我的腦海中:桃李不言,下自成蹊。
李老師的行動本身就是在寫字,就構成一本書。要從他所寫的文字讀,也要從他的行動中讀,更要從他的心意去讀。
學生時代我們還年輕,思路也會很清奇,去留意一些本不值得一提的小事情。比如,有一次,李老師的手纏上了紗布,我們好奇這是怎麼回事。李老師說是在家燒水,往壺裡灌的時候給燙着了。
我們幾個同學私底下交流:這麼神的學術大牛,在家裡還要親自燒水的嗎?各種八卦、腦補,模拟了各種情節,探讨各種可能性。最終,幾個小夥伴得到了一個巨大的發現:李老師應該也是普通人!生活中終究還是要做些家務的!
李老師接受采訪時,有時會帶着我,我給幫忙打燈補補光。現在我拍視頻,經常還能想起來給他打燈補光時候的樣子。
有時,他請外國教授吃飯時會帶上我。有一次,在王府井的“萃華樓”飯店請高坂教授吃飯。席間話題主線,大概是關于基層社區組織有關系的内容。第一個印象深刻的是:一個日本教授居然通過讀書,就可以對中國基層的派出所、社區、物業等各種機構的關系如此了解,比我這個自小生活在中國的人了解得更清楚,真是慚愧:自己在中國活這麼多年,算是白活了!
另一個印象深刻的就是:李老師很喜歡吃烤鴨的鴨頭!真的很喜歡!看他吃鴨頭的樣子,真是太香啦!
之前我從來沒吃過,甚至不知道那個部位居然也值得吃?!不過,從那頓飯之後,基本上每次吃烤鴨,我都會品品鴨頭。同時,會不自覺想起李老師。後來,看到一個心理學理論說:一旦某種記憶與“味覺”聯系在一起,印象就會更深刻了。說是因為這記憶和味覺會調用大腦神經系統的同一片區域。這理論不知真假,從實際體驗來看,這好像是真的有聯系。
清華社會學系複系後的第一年,學生很少,隻有5個,而且,周虹雲師姐還經常神龍匿蹤。人太少,就沒啥集體活動,好處是與老師吃飯的機會倒是挺多。李老師不挑,下館子行,到食堂吃碗面也行。
第二年,學生多起來了,熱鬧了,居然可以組織集體活動,比如唱歌、打球了!
有一次,老師一隊、學生一隊,打籃球賽。意外發現,李老師跑位相當靈活,投籃也很準。我們這些年輕學生去防守,甚至會被撞飛。當時就很感概:他們很強很能打啊!這種敢打敢拼的精神頭兒,一直感染着我。
20年過去,我現在已經快到了老師們當年的那個年紀了。遙想當年李老師他們重新創辦這個系,協調各種關系,尋找各種資源時,所承受的壓力應該也不小吧!内心是否也有不少焦灼呢?與我們現在遇到的焦灼,是不是類似呢?他們是怎麼排解的呢?
而今,不少老師已經退休,甚至撒手人寰。不禁感慨,不知20年之後我是否還活着?如果已經死去了,會給這個社會留下點什麼嗎?
四、生死
2003年,碩士馬上要畢業的時候,舅舅從老家給我來電話,平靜的語氣中,傳來晴天霹靂般的消息:我母親診斷出癌症!
走在北三環的立交橋大喊:老天爺,你安排的命運太不公平了!單親母親把我和妹妹拉扯長大,我要畢業能賺錢了,她可以享福了,卻又得了這麼嚴重的絕症!老天爺也不知聽到沒有,反正是沒啥反應,滾滾車流持續轟鳴!于是,擦幹眼淚,趕緊設法全力以赴給母親治病。
電話求助李老師。李老師立即請師母給我打電話,她熱心地幫我聯系到北京腫瘤醫院住院。師母在電話裡安慰我:現在治療癌症有成熟的方案,不用太擔心,都很标準化。我問了關于是不是要買補品的問題。她耐心的給我分析,建議我把錢花在刀刃上。
李老師還安排給我打了幾千元救命錢,對于本就窮困的我,幫了大忙。
當時,我的社會經驗很少,聽說在醫院都是要給醫生送紅包的。盡管很拮據,也打算給師母介紹的那個大夫一些紅包,讓她設法全力以赴給我母親好好治療。但是,人家堅決不收。跟我說:你看你在清華念書,這麼現代化的一個人,怎麼能送紅包呢?!
對我而言,這其實也是一個教育。有時越傳越邪乎的傳言,未必是真的,要相信社會自有善的力量、自然行着正道。
感恩李老師的地方很多,卻一直不知道該怎麼報答。那次為了感謝李老師幫助救母親,我聽從舅舅的建議,給李老師帶了老家的特色白酒。送到李老師家的時候,他堅決不收。建議我送給需要求辦事的人。看老師堅決不收,我還挺尴尬的。
後來,社會經驗慢慢多起來之後,我才知道,酒不可能是李老師的心頭好。
除了我所見到的那層天,還有很多層天;
除了我能看見的那種人,還有很多種人。
慣習和場域,讓人和人之間的認知和行為差異巨大。
這是從李老師的一言一行和微妙互動這本無字書中得到的啟發之一。
那麼,李老師給我最大的啟發是什麼呢?我想應該就是:多元求真。
針對學生,他是有個性化的指導,因材施教,尊重學生的選擇;針對社會學系的重建,不拘一格降人才;對社會現象,以多元的視角,多理論多角度審視,多種數據源交叉驗證。
一個社會,當隻能有一種理論、一套語言,并且一定要某某壓倒一切的時候,可能已經病得不輕了。
多換換角度看問題,多多與人共情,尤其是與弱勢群體共情,是如此難得,卻又如此重要。因為那是看到真相、求得真理、讓人人可以有活路、社會可以長治久安的必由之路,也是通往智慧人生的不二法門吧!
前幾天,看到李為老師的紀念文章中提到,李老師說:“我也讀過唯識學的書籍,知道唯識是大乘佛教的基本觀點,是說這個世界的一切事物都是因緣和關系而暫時出現的。”
這讓我有點意外。從未聽過李老師講過這些心法。如果當年我上學的時候,他說這些,我肯定是無法理解聽不進去,甚至嗤之以鼻的!而如今,隔着時空看這些文字,再想想唯識宗的法意,似乎能讀懂一點李老師的心意了。
身體是因緣和合,終歸會散去。但是,把“我”放小、把衆生放大的人生智慧,以及通過用心觀察嚴謹論證而寫就的深刻理論創見,卻會照亮一代又一代人,閃爍在字裡行間,熠熠生輝而不朽。
謹以此文悼念李強先生!
此生有幸讀到您,但願有緣再相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