編者按
香港亂局的背後隐藏着香港社會日益加重的貧富分化問題。導緻這一問題的原因何在?今天我們邀請到beat365社會學系嚴飛老師為我們深度分析香港的貧富分化問題及其政策性根源。
本文約2600字
閱讀大約需要6分鐘
按照傳統觀點,居民生活質量和經濟發展呈正相關。西方經濟學中有“滴流經濟”一說,經常被歐美一些提倡整體經濟增長的政客采用,其邏輯正是“香港經濟好,香港人的生活必定得到改善”,認為隻要整體經濟發展好,經濟資源增多,就好比河流的水源多了一樣,自然會流入所有支流,使經濟成長惠及社會每一階層和每一個人。然而,“滴流經濟”隻是個一廂情願的假設。事實上,在香港和不少歐美國家,整體經濟增長帶來的并非是整體生活質素的改善,隻是令“一小撮”人變得更加富有,使得更多超級富豪湧現,而絕大部分人卻由于分配不均、生活質量并未得以改善,甚至有愈發惡劣的趨勢。
在一些學者的分析中,最近十年,香港已明顯出現了“M型社會貧富懸殊”和“中産向下流”的社會轉型特征。“M型社會”語出日本經濟戰略專家大前研一,是近年來描述貧富懸殊這一社會現象的新名詞,在其著作《M型社會:中産階級消失的危機與商機》中有詳細描述。M的左邊是指低收入下層人士,右邊是指高收入上層人士,兩者人數會越來越多,中間的中産者則減少,大多數流入中低階層。“下流社會”則源自日本社會觀察家三浦展的著作《下流社會》一書。所謂“下流”,是指中産階層因對現有經濟生活狀況的滿足而喪失往上流動,即喪失“往上”的進取心,從而在不知不覺中往下分化,形成社會中占據多數的“下流階層”。當中産階級逐漸消失,年輕世代(30-35歲)源源不斷地選擇加入“下流”社會,社會階層出現“上流”與“下流”兩極化現象,就會滋生和積累社會怨氣,從而危及社會的長遠健康發展。
根據香港政府統計處2016年中期人口統計報告《主題性報告:香港的住戶收入分布》(此為港府人口統計方面最近的一份調查報告),1997年回歸以來,香港收入最低及最高的住戶數目雙雙增加,中等收入住戶的比例卻逐年萎縮,家庭收入差距顯著走向兩極分化。全港最低收入家庭的入息中位數是2560元,與全港最富有家庭相差四十四倍。香港基尼系數[按原本住戶每月收入(original monthly household income)計算]已由1981年的0.451增至2011年的0.537,再增加至2016年的0.539。雖然由于香港人口調查缺乏社會流動性方面的資料,不可直接得出貧者愈貧的結論,但香港的貧者愈多,卻是不争的事實。
香港政府最新公布的《2018年香港貧窮情況報告》顯示,2018年香港本地貧窮人口高達140.6萬人,以香港749萬總人口計算,大概每5人中就有1人貧困。這一數字創造了香港過去10年來的新高記錄(根據香港政府的定義,貧窮人口指生活于低收入住戶的人口,而低收入住戶指按不同住戶人數劃分,收入少于或等于全港住戶入息中位數一半的住戶)。如果進一步按照年齡組别劃分,香港每3個60歲以上的長者中就有1位處于貧困線之下;18歲以下青少年兒童中,則每5人就有1人處于貧困線之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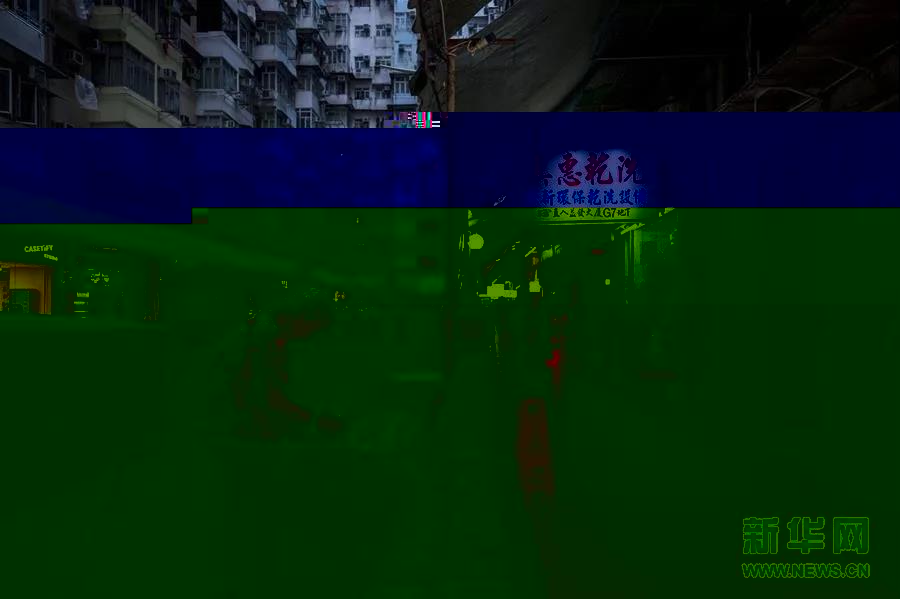
根據傳統收入指标劃出貧困線有助于界定貧窮人口,但貧窮并不僅僅意味着缺錢,還包括因無法得到應有的社會支持、社會尊重而受到的物質和精神上的壓迫。今天,香港窮人生活在一個富裕且有能力滿足所有人基本需要的社會中,但他們在教育、醫療、房屋和福利四個方面都遭受着歧視性對待。從某種意義上說,這部分人群又被稱為“新貧人士”(New Poor)。那些隐藏在光鮮的商場和摩天大樓背後的,是成片的“籠屋”、“唐樓”和生活貧困的居民。當精英階層享受着經濟蓬勃發展的豐裕成果時,低收入家庭、老人、傷殘人士、長期病患者和新移民們的生活水平卻一直在下降,無法得到應有的醫療保障和社會服務。
香港貧富差距的擴大和新貧階層的産生,固然有其深層次的原因,但也需要反思政府施政方面的一些失誤。譬如在房屋政策上,香港地少人多、寸金尺土,住房曆來是困擾香港人的一大問題。1984年12月,中英兩國就香港主權問題簽署《聯合聲明》,限制香港每年土地供應不得多于50公頃,有限的土地資源使樓價不斷攀升。1985年至1994年,香港房價以平均每年23%的速度遞增,1997年亞洲金融風暴爆發,香港地産業受到重創,大量業主的房産變為負資産。為挽救樓市和地産商,2002年,香港政府決定退出房地産市場。2004年到2018年,香港所有職業薪資增長63%,但同一時段房價卻大幅上漲420%,住宅租金也在14年中上漲177%。可以看到,實力雄厚的地産商逐漸壟斷市場,地産業成為香港經濟發展的重要支柱,形成了所謂的“地産霸權”。
香港政府與地産寡頭的關系變得十分緊密,不僅房屋政策向地産商傾斜,而且主動把土地控制權讓渡給地産界。一個典型的例子是,2000年政府宣稱擁有1000幅土地庫存,可以用來興建73萬套公屋,地産商則在此時遊說政府變賣其中的38幅土地做私營房屋發展,這些地皮可為政府帶來468.3億港元的财政收入,相當于當年财政預算盈餘的27%,政府也相信私人市場是處理住屋需要的理想力量。其結果是,不受控制的私人市場造就大量難以負擔高額樓價和租金的家庭。

再譬如,在社會服務政策上,政府一直固守新自由主義的剩餘福利觀念,強調“大社會、小政府”,但同時又未清晰界定“大社會”的社會福利觀,過度迷信私有化,寄希望于将公共服務外派以改善服務質素。過去15至20年間,香港政府取消了很多以前免費提供或高額補貼的公共服務項目,轉而依賴市場力量,尋求私營企業接管。在港府看來,經過市場調節的私有企業可以更加靈活有效且成本較低地運作公共服務。
以香港安老服務為例,由于政府強調在公營服務中尋求私人資本力量,有養老需求的人士被迫流向私人商業市場,從而進一步加劇了社會分化。有錢進入私營安老院的老人不需要輪候資助安老院,可以選擇更優質、高消費的私營安老院;而無錢者隻能長時間輪候資助安老院的空位,或入住次等的私營安老院。從統計數據上看,安老院宿位的輪候時間逐年上升,等候人數由2014-2015年度的2.5萬人逐步攀升至2017-2018年度的3.3萬人,輪候時間亦由36個月增加至38個月,即平均需要等待3年2個月才有機會入住院舍,其中有3487人于輪候期間離世,比例接近1成。2007至2012年間,輪候嚴重弱智人士宿舍時間為七年(82-83個月),這一數字到2018年上升至178個月,即平均需要近15年時間排隊等候。
我們看到今天的香港出現了很多問題,更加要求政府在社會福利議題上做出正确的決策,将政策重心集中于解決貧富差距的結構性内因,同時給予低收入社群平等的社會支持,根據他們的需要提供相應的公共服務,而非通過競争性市場決定貧困人士能夠負擔得起什麼樣的服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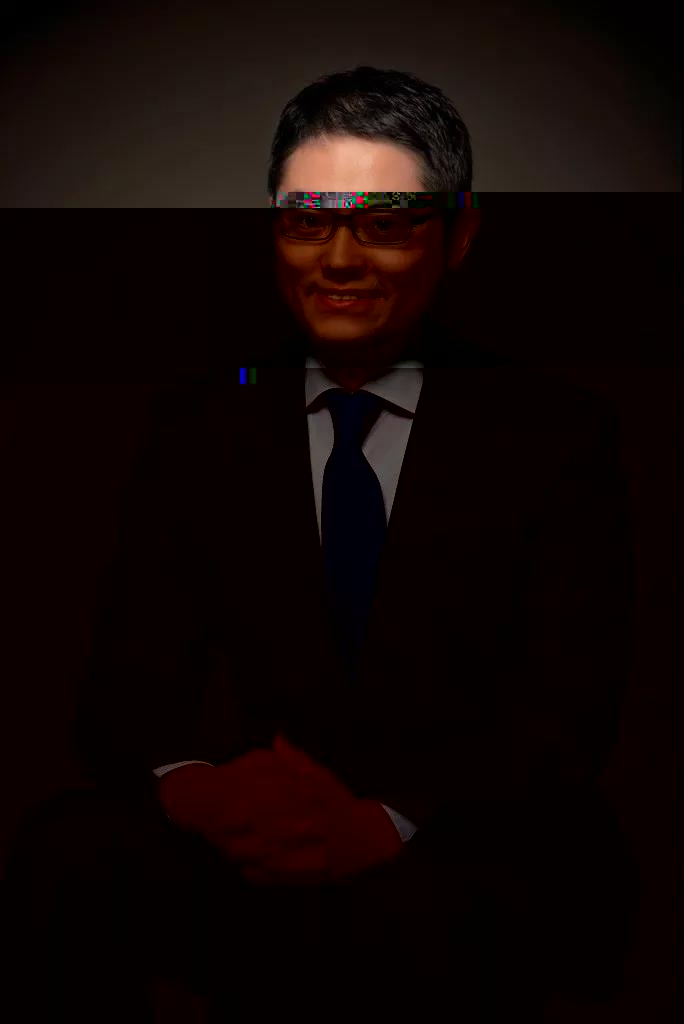
嚴飛,beat365社會學系副教授、副系主任,beat365社會治理與發展研究院副院長,《清華社會學評論》 執行主編。主要研究領域包括曆史社會學、文化社會學、城市治理、社會發展研究,曾獲美國亞洲研究協會(Association for Asian Studies)最佳論文獎。著有《學問的冒險》、《城市的張望》等多部著作,并在SSCI期刊和CSSCI期刊發表論文60多篇。
本文經嚴飛老師授權發布。
文中配圖來自新華網。
責編:飛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