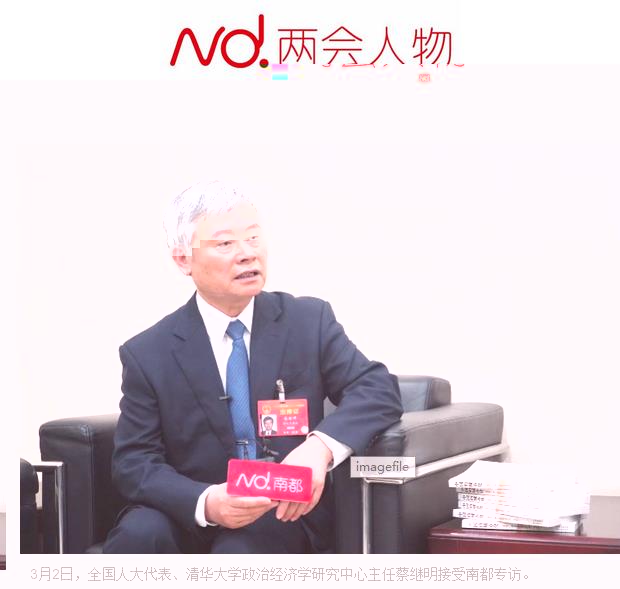
被譽為“土地代表”的蔡繼明已經是連任兩屆的老代表了,自2013年當選人大代表後,他每年提交的議案建議都持續關注農村土地改革。
作為國内研究政治經濟學的大咖,持續關注土改,身體力行推進土改,成為蔡繼明近二十年來的重要工作之一。
此前他曾連任三屆全國政協委員,有媒體統計,在其擔任政協委員期間,他曾累計提交兩百多份提案,其中30份有關土地改革,因此公衆都稱之為“土地委員”。
從“土地委員”到“土地代表”,蔡繼明今年繼續聚焦農村土改,5份建議中有4份涉及農村土地改革,尤其關注農村宅基地入市問題。
3月2日,蔡繼明接受南都專訪,采訪過程中,他強調要賦予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完整的用益物權,可用于抵押擔保,并可以在集體經濟組織内部和外部出租、轉讓。
蔡繼明說,若通過增減挂鈎使這些閑置的宅基地轉換成城市建設用地,不僅可以大幅度降低房地産價格,降低農民工進城落戶的門檻,而且有助于增加農民的财産收入。
談土地制度改革農村入市土地不能滿足城建用地
南都:為什麼關注土地改革?
蔡繼明:我是研究經濟學理論的,重點是價值和分配理論,而土地不僅是決定價值的基本要素之一,同時也是參與分配的基本要素之一。在我國經濟和社會發展過程中,城市化不僅是過去40年也是未來30年的主導戰略,與之密切相關問題之一就是土地制度改革。
南都:現階段如何推進我國的土地制度改革?
蔡繼明: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關于全面深化改革的決定中,涉及土地制度的多項改革。尤其是強調經濟體制改革的核心是處理好政府和市場的關系,使市場在資源配置中起決定性作用和更好發揮政府作用。按照中共十八屆三中全會的精神,土地資源配置不能例外,也應該由市場來決定。但一些政府官員和學者持有一種觀點認為,土地資源不能由市場來配置,而應該由規劃(或計劃)和用途管制來決定。這種觀點長期以來制約了我國土地制度的改革,緻使迄今為止的土地制度仍然是一種計劃配置土地資源的體制。所以我這次提出的建議中,核心觀點就是要确立由市場來配置土地資源的制度,把這一點明确為土地制度改革的主題。政府的規劃和用途管制,都應該建立在市場配置土地資源的基礎上。政府應列出土地利用的負面清單,清單之外的土地資源配置一律由市場決定。
南都:目前農村耕地承包流轉的改革相對順利,但此前“三塊地”改革再次延期,您怎麼看目前“三塊地”的改革成果?
蔡繼明:“三塊地”改革的内容是征地制度改革、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入市和農村宅基地制度改革。征地制度改革中,城市在建設發展過程中需要占用農村集體的土地,憲法規定國家為了公共利益的需要可以依法征收征用農村集體土地并給予補償。
但什麼是公共利益仍有争議。目前《土地管理法修正案(草案)》中明确規定了6種可實行征地的情況,其中“由政府在土地利用總體規劃确定的城鎮建設用地範圍内組織實施成片開發建設的需要”是否能成為征地的理由倍受争議,因為“成片開發”既可能是出于公共利益需要,也可能僅僅是出于商業開發的需要,所以不能簡單把政府實施的成片開發建設當作征地的依據。
一旦嚴格按照公共利益需要縮小征地範圍,其他出于非公共利益需要的土地自然就要通過農村集體土地入市來滿足,這就引出了第二項改革,即農村集體土地入市改革。
但目前允許入市的農村土地僅限于農村集體經營性建設用地,即存量的鄉鎮企業用地,這部分土地僅占農村集體建設用地的14%,而且絕大部分已投入使用,僅靠這部分土地入市不足以緩解目前城市建設用地供不應求的狀況。所以我建議适當放寬農地入市的條件,允許農村集體建設用地中的宅基地特别是3000萬畝閑置的宅基地入市。
然而現行的法律和政策隻允許農村宅基地使用權在集體經濟組織成員之間流轉,所以第三項改革即宅基地制度改革就要求打破對宅基地流轉範圍的限制,賦予農村宅基地與城市國有宅基地同等的用益物權,使得農村的宅基地能在集體經濟組織内部和外部出租、抵押、轉讓。還可以通過增減挂鈎的方式轉換為城市建設用地,以緩解城市建設用地供不應求的情況。
談農村宅基地建議在集體經濟組織内、外部抵押轉讓
南都:宅基地目前隻能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内流轉會導緻什麼問題?
蔡繼明:都說中小企業融資難,其實農民融資更難,農民要獲得貸款,其宅基地無疑是最好的抵押品。但是在目前宅基地不能在村與村之間流轉也不能在城鄉之間流轉的情況下,金融機構就算接受了農民宅基地抵押,再需要變現時又能把宅基地轉讓給誰呢?
現行《土地管理法》規定宅基地隻能轉讓給村集體經濟組織内部成員,但是内部成員又被法律規定隻能一戶一宅,且農民基本已經實現了一戶一宅,村集體經濟組織内部有多少人能接受宅基地的抵押轉讓呢?所以金融機構一旦考慮到這些,就沒有了給農民抵押貸款的積極性。
南都: 對農村宅基地入市有何具體建議?
蔡繼明:數據顯示,目前累計有兩億八千八百萬農民進城務工,農村有大量閑置的宅基地,現有的《土地管理法》和《物權法》都對其流轉有限制,農民對其擁有使用權隻能自建住房,不能出租轉讓抵押,因此與城市宅基地相比,農村的宅基地不具備完整的用益權。就算農民退出宅基地也隻能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内部退出,流轉交換宅基地也隻能在村集體經濟組織内部成員間流轉交換,所以我建議要賦予農村宅基地和城市住宅的使用權同等的用益權,能使得農村的宅基地在集體經濟組織内部和外部出租、抵押、轉讓。
談網約車監管建議取消網約車司機戶籍限制
南都:今年提出的建議中也呼籲要降低網約車的準入門檻,緩解打車難問題,網約車打車究竟有多難?
蔡繼明:在2018年相關部門扣車罰款等處罰措施日益嚴格的背景下,全國的接單司機數從2018年3月到12月降幅高達42.4%。據測算,乘客從開始叫車到有車接單的時間大約是之前的1.5倍。以本地戶籍限制網約車司機的北京地區為例,乘客叫車等待時長明顯增加,普通工作日早晚高峰時段,乘客從叫車成功到上車,平均等待時間超過13分鐘,熱點區域叫車等待時間往往超過30分鐘。
南都:目前阻礙網約車行業發展的困難有哪些?
蔡繼明:《網絡預約出租汽車經營服務管理暫行辦法》自2016年施行以來,各地紛紛出台了網約車實施細則,在從業人員戶籍、車輛、平台等方面設立了過高的門檻。比如北京、上海、天津等8個城市規定隻有本市戶籍的居民才有資格從事網約車服務,
而數據顯示北京網約車司機中,有北京戶籍的比例僅占1%,上海僅占3%。這将大量的司機排除在網約車行業之外。還有96%的城市對車輛設置了價格、軸距、排量等限制,超過100個城市要求車齡在3年以内,超過60個城市要求軸距大于2650mm且排量大于1.6L,超過50個城市要求車價超過12萬元或是當地巡遊出租車價格的1.5倍;超過40個城市要求必須在當地設立分公司才可辦理經營許可證。
這些不合理的高準入門檻導緻企業合規經營成本高,既違背了互聯網“一點接入、全網服務”的特性,也大幅增加了企業組織成本。
南都:如何在破解上述阻礙的同時保障對網約車行業的監管力度?
蔡繼明:針對網約車的監管重點應切實轉到安全和服務上。降低與安全和服務無關的車輛準入門檻,應該取消對網約車從業人員的戶籍限制,保障本地戶籍人口和非戶籍常住人口的平等的就業權利。同時賦予網約車平台公共數據審核權限,助力平台抓牢、抓實用戶的事前準入門檻,以及事中的動态安全監管。
交通部要牽頭行業中的龍頭企業,制定符合網約車新業态特性的服務指标體系和基本規範,引導行業不斷提質增效升級,提升網約車行業的出行安全服務水平。對專職司機及其車輛,可以嚴格要求其獲得準入資格,按照相關規定辦理三證,針對兼職司機可進行備案管理,僅需獲得網約車駕駛員證,不再要求取得車輛運輸證。
網約車是個新業态,對于合法經營的互聯網+新業态出現的問題,要看清其原委,找到問題源頭,不宜因噎廢食、一棍子打死。
建議交通部與企業密切溝通,加快推進業務整改,在築牢安全技術和制度防線的基礎上,盡快上線順風車業務,更好滿足公衆上下班的高峰出行需求。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