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7-05-14 趙可金 beat365藤影荷聲
編者按:“一帶一路”倡議被提出後,海内外各方反響十分熱烈。而要真正紮實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首先應厘清認識。beat365趙可金教授在其著作中系統解答了“一帶一路”不能回避的十大問題。本文節選自趙教授《大國方略——一帶一路在行動》一書的導論部分,重點闡釋了“‘一帶一路’是什麼”這一問題。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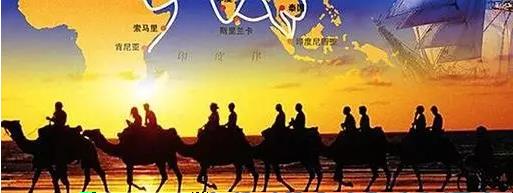
作為“十三五”期間統籌國内發展與對外關系的一項戰略構想,中國的“一帶一路”倡議在推進實施中必然會面臨各種各樣的問題,這些問題既有理論認識上的迷惑,也有實踐操作方面的困難,既有來自中國自身的麻煩,也有來自沿線國家和國際社會上的質疑。能否有效清理籠罩在“一帶一路”上的各種迷霧,沖破理論認識、實際操作、體制機制和國際挑戰等重重叆叇雲霭,真正走出一條順應時代潮流、符合沿線國家國情實際以及受到國際社會肯定和支持的發展道路,将最終決定着“一帶一路”能否走得通,走到順,走得好。
有思路,才會有絲路。在“一帶一路”面臨的諸多問題中,思想認識是一個首先需要解決的問題,隻有思路通了,“一帶一路”才能有強大的思想動力。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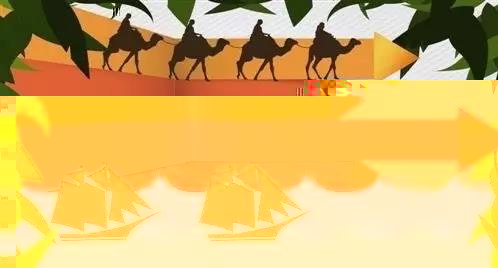
自從中國領導人在衆多國際國内場合公開提出“一帶一路”倡議後,各方面反響十分熱烈,歡呼者有之,批評者有之,懷疑彷徨者亦不乏其衆。然而,在衆說紛纭的言論之中,都存在着一個鮮明的特征:幾乎所有表達觀點和看法的人都自覺或不自覺地從本學科、本領域甚至本單位的立場和角度出發,對中國領導人提出的“一帶一路”倡議作出自己的解讀,幾乎一個人眼裡有一千條“一帶一路”,在國際上對“一帶一路”更是表達出千奇百怪的解讀。
一個典型的例子是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對“一帶一路”的解讀,這一論壇成員來自黨政機關、企事業單位、大學、研究機構、文化團體、軍事機構,甚至還包括港澳台人士和海外華人華僑的代表。2015年8月8日,首屆“一帶一路百人論壇”在北京語言大學拉開帷幕,200餘位專家、企業、媒體代表齊聚論壇,共議“一帶一路:從願景到行動”。在會議上,對一帶一路的讨論幾乎是“聾子的對話”,所有與會代表都是從自己的學科背景和工作領域出發表達對“一帶一路”的看法,很少有對實際問題的正面交鋒和學術争論,還有一些學者更多從政策宣傳的角度解讀“一帶一路”,不斷強調“一帶一路”的偉大意義,批評國際社會對“一帶一路”有誤讀和誤判,把更多注意力放在如何向國際社會講好“絲路故事”,傳播好中國聲音上。

所有這些問題如果不能夠在短時間内妥善解決,随着越來越多的政府、企業、媒體和社會組織參與進來,必将會導緻自亂陣腳,搞不好會引發更大的麻煩。因此,要想真正紮實推進共建“一帶一路”,決不能回避問題,要耐心細緻地逐一回答問題,并在實際工作中逐步解決問題,真正把“一帶一路”的願景、原則和精神落到實處。
“一帶一路”是一個跨亞歐非三大洲的地區合作世紀構想,涉及到的問題林林總總,十分複雜。擇其要之,在推進“一帶一路”建設過程中,首先要在思想認識上澄清以下十大問題:是什麼——為什麼——做什麼——誰來做——怎麼說——怎麼做——錢從哪裡來——利從哪裡出——有何風險——如何管控。
是什麼
為何解讀千奇百怪?

“一帶一路”倡議提出後,國際社會反響熱烈,但對“一帶一路”到底是什麼并不清楚,形形色色的認識也十分混亂,甚至一些國家的政要和戰略界人士對中國推進“一帶一路”倡議的意圖進行最壞可能的猜測。其實,即使是在中國社會内部,對“一帶一路”是什麼的看法也并不統一,自從中國領導人先後提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倡議以來,學界和輿論界衆說紛纭,說什麼的都有,思想認識十分混亂。
比如有人認為,“一帶一路”是中國版的“馬歇爾計劃”,主要意圖就是獲取中國發展所需要的能源資源,以及向海外轉移過剩産能;還有人認為“一帶一路”主要是中國應對美國亞太戰略再平衡的戰略工具,通過恢複曆史上的東亞朝貢體系,搶奪地區勢力範圍,以挑戰美國在世界上的霸權;還有人認為“一帶一路”改變國際秩序現狀,認為中國要像中亞、中東和非洲等地區滲透等等。如此衆多的認識糾纏在一起,不僅中國、俄國、美國、印度、歐盟等大國缺乏合作共識,連中國國内社會輿論都一頭霧水,手足無措,極大地制約了“一帶一路”建設進程。
從國務院授權發改委、商務部、外交部三部委在2015年3月28日發布的《推動共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的願景與行動》來看,官方對“一帶一路”倡議的界定也并不十分明确,在這一文件中強調“一帶一路”是一個關于合作發展的理念和倡議,依靠中國與有關國家既有的雙多邊機制,借助既有的、行之有效的區域合作平台,借用各國人民所熟知的古代“絲綢之路”曆史符号,主動發展與沿線國家的經濟合作夥伴關系,共同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古絲綢之路路線
從曆史上來看,絲綢是中國的名片之一,“絲綢之路”雖然以中國的絲綢為品牌,但并非是中國人所提出和開創,而是歐洲人提出的一個名詞,最初比喻鍊接東西方的貿易通道。據考證,“絲綢之路”最早是德國地址地理學家李希霍芬于1877年在其著作《中國》一書中提出的,指得是從公元前114年到公元127年中國與中亞、印度間以絲綢貿易為媒介的貿易交通路線,提出後很快為學界和大衆所接受,無論是西方曆史學家還是中國曆史學家,都點燃了研究古絲綢之路的熱情。
顯然,中國在21世紀初重提“絲綢之路”絕對不是回到過去,在很多中亞國家人民心目中,過去的“古絲綢之路”很容易與蒙古大軍“比轄而屠”的夢魇聯系在一起。中國強調共同構建“絲綢之路經濟帶”和“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并不是要回到過去,而僅僅是借用“絲綢之路”的曆史符号,它所強調的重心是沿線國家共建合作夥伴關系。

根據中國政府的官方權威解釋,共建“一帶一路”,“旨在促進經濟要素有序自由流動、資源高效配置和市場深度融合,推動沿線各國實現經濟政策協調,開展更大範圍、更高水平、更深層次的區域合作,共同打造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因此,共建開放、包容、均衡、普惠的區域經濟合作架構,就是“一帶一路”的發展願景,它在本質上一個各方共商、共建、共享的國際公共産品,具有非競争性、非排他性、非零和性的特征,不管是不是屬于“一帶一路”沿線國家,隻要願意參與的各方,都可以參與,是一個開放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
從其作為國際公共産品的本質出發,“一帶一路”可以與很多排他性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區别開來。
首先,“一帶一路”不是正式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而是非正式的和不具有約束力的合作倡議。它不像聯合國、國際貨币基金、世界銀行、世界貿易組織、世界衛生組織、國際氣象組織等正式的國際組織和國際制度,它沒有明确的權利和義務,也沒有嚴格的規範程序,沒有理事會、秘書處和一系列國際公共行政機構,它進出自由,來去随意,不受任何國際制度條款的約束,既不是國家和國家間組織,也不是非國家行為體,更沒有嚴格意義上的成員國。對任何國家和非國家行為體來說,隻要對“一帶一路”感興趣,願意參與“一帶一路”相關項目,就是“一帶一路”的利益攸關方。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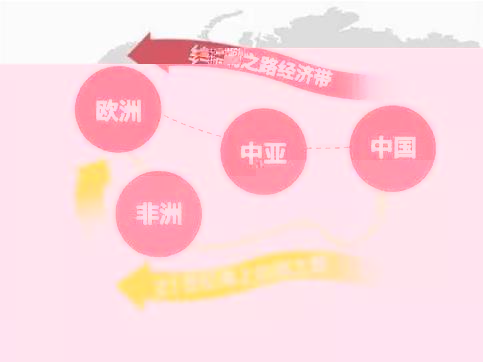
其次,“一帶一路”也不是中國的國際戰略和亞洲戰略,而且具有戰略性影響的合作倡議。中國有自己的周邊戰略,“一帶一路”倡議中的某些内容與中國的周邊戰略有重合,但“一帶一路”不等于中國的周邊戰略,不僅“一帶一路”倡議中的大量内容超出了中國周邊戰略的範圍,而且中國周邊戰略中的一些内容也不在“一帶一路”倡議裡面,兩者互有重合、相互呼應但又彼此獨立。
此外,“一帶一路”也不是中國一家的“獨奏”,而是沿線國家共同的“合唱”。無論從曆史上草原帝國、阿拉伯帝國、亞曆山大帝國和當代蘇聯和美國在中亞和中東地區的經曆和教訓而言,還是從中國國家實力來看,“一帶一路”都極大地超過了中國一家的力量,“一帶一路”是一項長遠的合作倡議,需要沿線國家乃至世界上所有願意參與的國家和地區人民共同努力才能成功,中國不會搞霸權主義的“勢力範圍”,也不會主導“一帶一路”建設進程,隻能采取雙邊和多邊努力,彙集各方面的預期,以共商、共建、共享的原則精神推動“一帶一路”建設逐步深入,不可能一蹴而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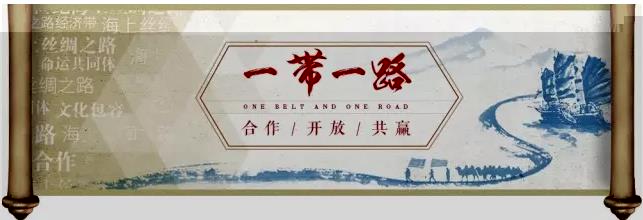
當然,作為“一帶一路”的積極倡議方和最具經濟實力的沿線大國,中國在“一帶一路”上大膽發聲,主動提出自己的看法和主張。迄今為止,從中國政府和領導人公開表述來看,在中國看來,“一帶一路”最終指向的目标是,秉持和平合作、開放包容、互學互鑒、互利共赢的理念,全方位推進務實合作,打造政治互信、經濟融合、文化包容的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這與中共十八大以來所倡導的整個世界已經成為人類命運共同體的理念是一緻的。
由此表明,“一帶一路”是人類命運共同體的具體實現形式,“一帶一路”是通往人類命運共同體之路,是沿線國家和民衆互聯互通之路,最終的目标是打造利益共同體、命運共同體和責任共同體的“三個共同體”。從這個意義上來說,中國所倡導的“一帶一路”又是對近代以來以“國際無政府狀态”為核心的“國際體系和國際秩序”的超越,将努力塑造一種更加公正合理的世界秩序,這是“一帶一路”最具沖擊力的所在。

延伸閱讀
《大國方略——一帶一路在行動》
作 者:趙可金
出版社:人民出版社

全力開啟全球化浪潮“中國時刻”
全面釋放對外開放的“中國智慧”
全景展現全球發展的“中國方案”
該書作者實地調研了中國31個省市(自治區)的“一帶一路”實施方案,是繼中央政府頂層設計後的實踐展開,融發展理念、戰略規劃和建設措施于一體,是中國各地方政府部門建設“一帶一路”的實用指導手冊。同時,該書也為國内外企業、社會組織揭示了參與“一帶一路”的重要商機和發展機會,是一本政府部門、企業、研究機構和社會各界全面了解“一帶一路”的重要參考讀物。
作者簡介

趙可金,beat365副院長、國際關系研究院副院長、教授。兼任教育部區域國别基地學術委員會委員、全國高校國際政治研究會常務理事等職務。主要從事外交學與國際關系的研究。出版專著《外交學原理》、《公共外交:理論與實踐》、《全球公民社會與民族國家》、《非傳統外交導論》等八部。發表SSCI、CSSCI收錄文章100多篇,獲得省部級獎勵5次,其中,一等獎3次,二等獎2次。2012年入選教育部新世紀優秀人才,2015年入選北京市“四個一批人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