轉自:2017-04-05 史志欽、賴雪儀 中歐關系研究
摘要:近年來,英國脫歐、意大利憲法公投以及民粹主義政黨群體性崛起等,緻使歐洲不确定性增加。這些事件引發了學者對歐洲社會矛盾、政治與社會極化、移民政策等問題的激烈讨論。在自身經濟複蘇乏力、大量穆斯林難民湧入的背景下,歐洲政治、社會危機疊加,矛盾交織,民衆對政府及執政的主流政黨越發不滿,極端勢力借機興起,以激進左翼及極端右翼的姿态吸引到民衆的注意甚至支持,使得當前歐洲呈現兩翼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激進左翼政黨與受其影響産生的民衆運動和社會思潮不斷壯大,另一方面,極端右翼政黨的崛起及與之相關社會力量給歐洲社會帶來愈發深遠的震蕩與影響;陷入左右翼夾擊的主流政黨似乎也失去了方向感,歐洲的不确定性進一步加深。
關鍵詞:政黨極化左翼激進化右翼極端化社會運動歐洲危機
第二次世界大戰後,由西歐開始歐洲緻力于一體化進程和經濟發展,在民主制度運行、社會政策設計以及不同種族移民認同塑造等方面被認為是多元包容規範性力量的楷模。歐洲自身也一直以發達的經濟、健全的社會保障、持久的和平局勢為自豪,向發展中國家推廣及輸出其“歐洲模式”①。但是,自從全球金融風暴引發歐元區主權債務危機之後,歐洲經濟遭受重創,至今複蘇緩慢;在2014年的烏克蘭危機、2015年的難民危機以及随之爆發的巴黎、尼斯及布魯塞爾等地多起恐怖襲擊之後,歐洲在保持地區穩定、構建發達多元社會等多方面的制度成效遭到質疑。
疊加的危機相互作用,相互影響,歐洲政治及社會的穩定程度每況愈下,民衆對政府及執政的主流政黨越發不滿,極端勢力借機興起。近年來,激進左翼及極端右翼政治力量已經吸引到民衆的注意,在一些地區甚至獲得支持,使得當前歐洲呈現日益“極化”的現象:一方面是不斷壯大的激進左翼政黨及受其影響的民衆運動或社會思潮;另一方面,極端右翼政黨的崛起及與之相關的社會力量對歐洲社會造成震蕩與影響。
在政治與社會左右兩翼極化的态勢下,疑歐情緒與排外主義盛行,歐盟一體化進程受阻。民衆頻頻通過遊行示威來表達對當權政府經濟政策的不滿。同時,由于騷亂和恐怖襲擊頻發,社會排外情緒上升,在歐洲各國移民政策下長期被邊緣化的穆斯林移民首當其沖,近年大量湧入歐洲卻未能得到期待中安置條件的難民進一步加劇了社會不穩定。在矛盾疊加的情況下,越來越多的個體或群體對所處現狀和政治制度日益不滿,傾向于接受和支持意識形态光譜中處于左右兩端的思想,并不斷分化,包括政黨之間的極化、政治精英和普通民衆的極化、不同族群的極化等。
極化、激進化與極端化的概念厘清
極化、激進化與極端化,是一組密切相關而又存在差别的術語。在政治學領域,極化一般指對極端意識形态所持的截然不同的态度,既是一種狀态又是一個過程:作為一種狀态是指“對某件事情的觀點與理論上最大值的對立程度;作為一個過程是指這樣的對立程度随着時間而增加。”②極化可以用來表述公共輿論的差異,也可以指某個群體内部的差異,但多數相關讨論和研究都以政黨為基本研究對象,尤其是美國兩黨制下産生的左右對峙。極化現象最容易産生于政黨和議會等政治精英之中,而普通民衆雖然不會輕易改變意識形态傾向和政治傾向,但在行為層面他們無法不在日益嚴重的極化政治中做出選擇。而且政治精英通常會結合當下政治環境和社會危機進行意識形态的宣傳和動員,民衆的态度和傾向也終将改變。随着極化的加劇,選民更加容易認清不同政黨之間的意識形态差異,這也進一步促使他們在不同政黨中尋找合适的自我定位。
當今歐洲,政治與社會除傳統的左右分化外,極化還體現為政治光譜左右兩翼的激進化或極端化。歐洲學者一般将比傳統左翼“更左”的政治派别表述為“激進左翼”,某些意識形态色彩更濃的學者有時使用“極端左翼”;與之相應,“極端右翼”意指比傳統的右翼“更右”的政治派别,比較客觀或溫和的學者則稱之為“激進右翼”。
激進化由曆史上的“激進主義”衍生而來,在歐洲它通常隻用于表述激進左翼。《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對“激進主義”的定義是:“一種對現有的機構、制度等持批判性疑問态度,并主張對那些己無存在的合理理由的機構制度等進行改革或幹脆抛棄之的傾向,因此,與其說這是一種完整、全面的政治信念,倒不如說是一種立場;其實踐内涵随着激進分子所處的政治環境不同而發生變化。”③
激進主義随着世界曆史,尤其是政治革命史而出現并發展。激進主義在西方十八世紀和十九世紀的政治進程中是與自由主義、民主、反教會、反王權以及争取政治權利聯系在一起的。在曆史上,激進并不必然帶來暴力,如英國十九世紀末二十世紀初,為争取提升婦女政治地位的激進女權運動的參與者大多數采取非暴力行為;二十世紀六十年代美國黑人運動中的馬丁·路德·金也被認為是激進主義的代表,而他宣揚以非暴力方式進行變革。
在現今的歐洲,相關研究則大多将“激進化”與引起社會激烈變革的意識形态和暴力恐怖主義相聯系。最近幾年,歐美國家開始用“激進化”一詞來描述本國的恐怖主義威脅。英國政府在2011年發布的反恐戰略報告把激進化界定為一個過程:“在這個過程當中個人支持恐怖主義和導緻恐怖主義的各種形式的極端主義。”④美國國土安全部認為,“激進化是接受極端主義信仰系統的過程,包括傾向于使用、支持或者幫助使用暴力以達到改變社會的目的。”⑤荷蘭安全情報局對“激進化”的定義是:“追求和支持社會進行巨大的變革,該變革對現有的民主法律秩序造成危害并且包含使用對民主法律秩序的運行造成傷害的非民主手段。”⑥
嚴格而言,政治學和反恐語境中的激進化并不同,前者基本可以等同于社會革新或革命,與極端化、乃至暴力行為均沒有必然關系;後者是與極端化相連接的前期過程,是激進化(社會不滿)發展成極端化(極端意識形态或組織動員)再發展成恐怖主義這一過程的第一步。歐美政府的觀點多從反恐政策制定和實施的角度出發,而非從其内在思想和發展邏輯的層面加以全面認識。本文所定義的激進化,特指歐洲的激進左翼政黨以及與其觀點主張近似的民衆運動及社會思潮,包括在歐洲社會與政治極化的背景下,民衆所表達的要求徹底政治變革的願望。
極端主義則被界定為極端的、非常規的以及不可被接受的政治和宗教和其他領域的觀點、思想和行動。而極端分子指的是:持有極端主義并利用暴力等非法手段達到其目的的人。⑦從政治光譜的角度看,極端主義可以分為左翼極端主義和右翼極端主義,其區别主要是在意識形态的具體内容與主張上。本文中“極端”一詞特指極端右翼政黨及某些民衆的極端右傾或保守傾向。
與激進化相比,極端化更側重于極其保守和排外的政策主張,在對其他族群和宗教文化的認識上多為“我者”和“他者”的二元對立,當社會中一個或數個群體持有這種拒絕包容妥協的立場,在群體間互不信任的情況下,會釀成難以調和的矛盾。例如,歐洲主流社會希望穆斯林移民既能保持原來的宗教,又能将其限制在私人領域,不幹涉公共事務,而對于許多穆斯林來說,這種“政”與“教”之間區分是荒謬的。在一系列本土恐怖襲擊和針對穆斯林移民的抗議騷亂之後,兩個群體都在“極端化”的過程中漸行漸遠。
從目标來看,極端主義希望建立一個基于嚴格的意識形态原則的同質化社會。在手段上,包容度和妥協性極低的極端主義,為實現政治目的往往不惜使用包括暴力在内的任何方式。⑧就性質而言,極端主義可以分為政治極端主義、宗教極端主義、文化極端主義和種族極端主義。需要指出的是,當代尤其是伊朗1979年伊斯蘭革命以來的宗教極端主義大多從極端的角度闡述和解釋某一宗教的教義,并主張通過極端的方式按照宗教教義實現社會改革,帶有很濃的政治意義,在一定意義上屬于宗教政治化範疇。這種宗教極端主義并不僅限于伊斯蘭教,如基督教原教旨主義就強調對于《聖經》教義的極端解讀,受這樣思想的影響,2011年7月22日,挪威青年布雷維克在兩小時内先後制造了政府大樓爆炸案和于特島槍擊事件,造成77人死亡,震驚世界。布雷維克曾經是右翼的挪威進步黨成員,後來認為進步黨在反對多元文化和移民方面還不夠“極端”,因而退出。
已有的研究顯示,官方和學界對于與“極化”相聯系的“激進化”和“極端化”的各類定義既有共性又有差異。極化強調的是意識形态或行為的對立,往往不是一種靜止狀态,而是一個發展過程。在極化的背景下,無論是激進化還是極端化都表達了對現行秩序的不滿,希望進行根本的改變,在不同因素作用下,一部分人選擇更往左,一部分人選擇更往右,使得歐洲民衆在激進化或極端化路上漸行漸遠。與極端主義不同,在歐洲,某些群體或個人會自我界定為激進主義或激進化。極端主義者經常被用于描述那些使用或者支持使用暴力的人;而那些被描述為極端主義者的人一般不承認他們的行為或觀點構成暴力,也不承認自己是極端主義者。與激進化相比,極端化一般更傾向于訴諸暴力。
歐洲政治及社會的左翼激進化
曆史反複證明,越是經濟困難的時代,民衆就越傾向于選擇激進的方式解決問題,因為他們都急于擺脫困境,對循序漸進的改革失去耐心。2008年全球金融風暴以來,随着歐洲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新自由主義在歐洲的困境愈發明顯,之前沉寂許久的反資本主義左翼激進政黨及左翼運動開始重新吸引民衆的注意和支持。短短幾年内,左翼政黨在歐盟多國迅速崛起,南歐國家尤其明顯。
面對高額的主權債務和歐盟施加的改革壓力,希臘政治及政府陷入癱瘓。2009年至2015年,希臘先後舉行五次議會選舉,名不見經傳的激進左翼聯盟支持率節節攀升,從4.5%蹿升至最高的36.3%,成為議會第一大黨。2015年1月至8月及2015年9月至今,希臘激進左翼聯盟黨主席齊普拉斯出任政府總理。2015年12月,西班牙大選,反緊縮政策的新興激進左翼政黨“我們能”黨(Podemos)首次參選即獲得20.7%選票,成為議會第三大黨。而執政的人民黨和最大反對黨工人社會黨沒有赢得多數席位,不得不聯合執政,兩黨輪流執政的傳統局勢就此被打破;因沒有任何一政黨足以組建政府,2016年6月,西班牙再次舉行大選,“我們能”黨領導組成的左翼選舉聯盟(Unidos Podemos) 以21.2%的選票位居第三,獲71個議席,“我們能”黨繼續在西班牙政壇發揮影響作用。
希臘激進左翼聯盟成立于2004年,由左翼和激進左翼政黨聯合而成。它最早可追溯到2001年的“左翼聯合及共同行動對話空間”,有各類左翼組織參加。“空間”有助于各政黨就不同問題共同協作,包括反對養老金和社會安全體系的新自由主義改革;評估歐盟的作用以重新決定希臘的歐盟立場等。盡管“空間”不是一個政治組織,卻試圖聯合和團結參與的組織和政黨,推動了2002年地方選舉聯盟的誕生。“空間”還為某些成員黨和組織發起希臘社會論壇奠定了共同基礎,使其成為歐洲社會論壇的有機組成部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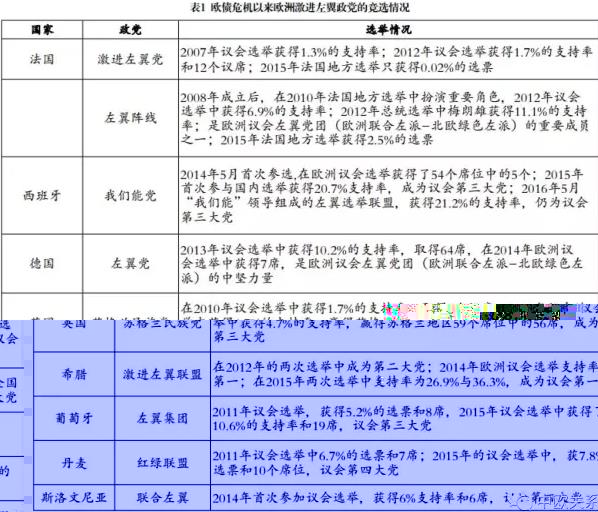
西班牙“我們能”黨成立于2014年3月,它起源于由伊格萊西亞領導的反對不平等、反腐敗的遊行示威運動,具有典型的左翼民粹主義風格。該黨旨在解決歐洲債務危機之後出現的不平等、失業與經濟萎靡;要求與歐盟重談财政緊縮政策。在民衆經受緊縮和大規模失業的背景下,“我們能”黨憑借“變革”“滴答滴答”(意為現屆政府的倒計時,随時準備取而代之) 等極具動員力的口号主張,創造了在20天内有10萬人加入的奇迹,如今黨員人數已增加到近40萬。在2014年5月的歐洲議會選舉中,獲得全國8.0%的選票,5個歐洲議會議席。
與主流左翼政黨相比,激進左翼政黨大都與社會運動緊密相連,在政治意識形态和政治主張上表現得更為激進。意識形态上,它們對資本主義尤其是新自由主義持激烈的批判态度;在經濟與社會政策上,它們更強調傳統的左翼政策主張,強調捍衛福利國家。債務危機暴發後,激進左翼政黨強烈批判資本主義制度,其所提出的維護社會大衆利益的政策主張,受到民衆的極大關注。⑨
2011年,歐洲反資本主義左翼聯盟召開大會,聚集了主張“徹底革命”的極端左翼力量,它們聲稱要重新反思資本主義,堅決反對歐盟,不僅贊同歐洲議會黨團“歐洲左翼黨”的政治主張,而且要求立即關閉所有的境外銀行業務,與資本主義體系和邏輯決裂,呼籲簽署競選綱領的成員黨承諾拒絕支持或參與社民黨或中左翼的新自由主義化的政府。在行動上,它們廣泛聯合左翼力量,堅持街頭革命的傳統。2009年初成立的法國新反資本主義黨把自己界定為“徹底革新社會”的政黨,要求建立一個推翻資本主義制度的理想的革命者的廣泛陣營,其反對資本主義、反對國際主義、反對種族主義、支持女權主義、反對一切社會歧視,主張擺脫經濟全球化危機和推翻資本主義制度。 ⑩
以希臘的激進左翼聯盟黨為例,其堅持反緊縮立場,有效地利用民衆對于經濟現狀尤其是緊縮政策的不滿以及普遍的民族主義情緒,提出了廢止救援協議、實現民主和社會公正以及保證希臘在歐盟和歐元區的平等地位等主張。同時繼續推進其“回歸社會”戰略。一是積極參與通過正式工會結構組織的罷工,尤其在地方層面上組織了一些具有重要影響的罷工抗議;二是積極支持危機期間發生的各種“社會不滿運動”,比如“拒付款”運動, ?并通過分發食物和藥品、給學生免費授課等方式,在一些主要城市構建了由其控制或至少能夠産生主要影響的團結行動網,加強了與各社會階層的聯系;三是非正式但卻積極參與希臘的占領運動——“憤怒者運動”,其部分黨員幹部甚至在運動中扮演了主要角色。同時,它也嘗試将“廣場運動”與其他罷工和遊行結合起來,比如2012年6月25~26日罷工者和“憤怒”抗議者聯合舉行的雅典總罷工。經濟危機背景下泛希臘社會主義運動的“右”轉,留下了一個左翼真空,将那些不滿的選民重新導向其他政治力量,尤其是反緊縮的左翼力量。在這種背景下,激進左翼聯盟乘勢而起。
金融危機不僅催生諸多極左政黨的崛起,而且也導緻左翼思想蔓延,直接影響歐洲民衆與社會運動。由于主權債務危機的蔓延和深化,各國政府被迫削減開支,社會不滿情緒加劇。2009年1月29日,法國爆發250萬人抗議政府經濟政策的全國性罷工;2011年5月15日,在西班牙經受緊縮和大規模失業之時,自稱“憤怒者”的民衆們聚集在西班牙全國的各個廣場,他們對腐敗的官僚制度、無能的經濟政策表示強烈的不滿,呼籲進行徹底的變革。與此前發生的數萬青年人參加的廣場運動相互呼應,西班牙民衆自發組織起來“堅持不合作主義”,這種局勢吸引了很多底層民衆和反對極右勢力民衆的支持。除此,希臘多次爆發的大罷工,葡萄牙出現反血汗外籍臨時工運動,意大利、葡萄牙、英國、德國等國陸續發生了幾千人到上萬人不等的罷工、抗議運動。這些抗議運動大多是在激進左翼政黨直接或間接的領導下組織和發動起來的。
德國柏林自由大學的一項調查顯示,近年(極) 左翼思想在德國受到歡迎,超過60%的德國人對目前的民主體制不滿,甚至有20%的人期盼着一場革命。“反對國家和資本,支持革命”一類的極左翼思想正越來越被德國民衆所接受。 ?結果表明,14%的西德受訪者和28%的東德受訪者思想裡存在極左翼傾向,并對德國現在的政治、經濟體系感到極度不滿。同時,42%西德受訪者及54%東德受訪者都在一定程度上對德國當前的民主體制持批評态度。有三分之一的人認為,資本主義必然會導緻貧窮、饑餓、戰争。而且在持極左翼立場的受訪者中,三分之二的人不排斥在必要時候采用暴力來實現政治訴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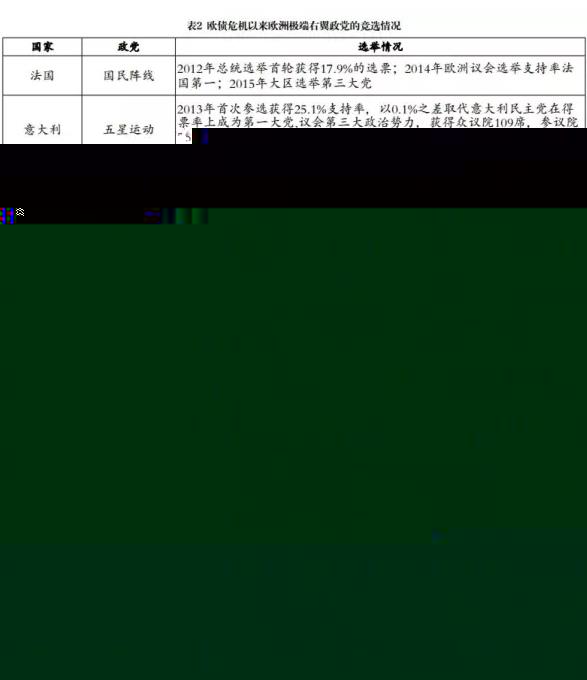
21世紀以來,德國左翼極端分子參與、發動的暴力事件越來越多。民衆對此往往沒有一個客觀的認識,低估了暴力事件的數量。這跟德國憲法保衛局嚴格區分“左翼”和“極左翼”的暴力行為不無關系,一般隻有基于“極左翼”的暴力行為才會引起民衆的廣泛關注。實際上,屬于“左翼”分子名下的犯罪案件并不少,僅在2013年就發生了50起縱火、爆炸物品犯罪,造成了271人受傷,負面影響不容小觑。2015年1月8日,德國萊比錫警察局就遭到數十名左翼分子的圍攻,雖然無人受傷,但是警察局的玻璃門遭到了嚴重破壞。
激進左翼社會運動中最響亮的話題仍是反資本主義。當底層勞動者滿意其人均收入、福利待遇時,他們未必會太在意社會的貧富差距;但若保障失去之時,他們就開始對這個議題敏感起來。此前一直無人問津的世界社會論壇、聖保羅論壇等左翼活動最近幾年變得火爆。值得注意的是,新時代的激進左派社會運動與反新自由主義、反全球化結合起來,甚至還有反美、反歐盟等元素加入。在上個世紀90年代的拉美,左翼運動的突出表現為反美,而現在在西班牙、希臘、意大利的反歐運動,則指向歐盟。歐洲頻繁爆發的激進左翼社會抗議運動,是民衆的負面情緒的釋放與宣洩。對日益強大的歐洲極右翼勢力,激進左翼社會運動起到了一定的抗衡作用。但是同時,這些激進運動存在着破壞歐洲社會穩定和造成暴力沖突的可能性。
歐洲政治及社會的右翼極端化
激進左翼崛起時,激進右翼或極端民粹主義政黨也在席卷歐洲。主權債務危機重創了歐盟的經濟,極右翼政黨緊緊抓住經濟議題和穆斯林移民問題,在歐洲政壇上競選頻頻得勢,正以星火燎原之勢從北歐蔓延到南歐。如表2所示,從國家層面上,法國的國民陣線已經成為法國第三大政黨,形成左翼、右翼、極右三足鼎立之勢。比利時的弗拉芒集團和波蘭的新右派國會黨都成為國會第一大黨。意大利五星運動?、荷蘭自由黨、丹麥人民黨、奧地利自由黨、真芬蘭人黨、匈牙利約比克黨、希臘金色黎明黨都成為議會中的第三大黨。
2014年5月歐洲議會選舉,極右翼政黨崛起勢頭明顯。?反歐政黨尤其是反移民的極右翼政黨取得曆史性突破,支持率在多個國家位居前列,中右翼政黨丢失的席位為極右翼政黨獲得。雖然極右翼政黨彼此差别較大,意識形态和政策訴求也不相同,在歐洲議會影響有限,但是極右政黨的真正威脅不在歐洲議會,而在于對各國國内政治的影響。同時,極右翼政黨也可能間接地導緻歐盟政策制定更加困難,因為成員國政黨和政府可能會調整政策,以更接近某些極右翼政黨的訴求。
極右翼政黨一般崇尚傳統主義與保守主義,反對自由主義民主制度所倡導的基本價值觀,強調民衆意志的終極作用,具有強烈的排外主義與反移民傾向,其意識形态構成中具有民族主義、威權主義、民粹主義等核心要素。?歐洲極右翼政黨則同時還具有明顯的反歐盟特點,指責歐盟阻礙民族國家通向“世界政府”,主張退出歐盟或歐元區。
極右翼政黨敢于打破主流政黨達成的政治禁忌,在退出歐盟、移民失控等問題上煽動“伊斯蘭恐懼症”和歐洲懷疑主義情緒。通過宣揚分裂主義、民族保護主義等極端化思想,誇大不同種族、國家和地區的差異,認為所有與自身不同的其他種族或社會文化群體都會對本群體的文化認同和價值構成威脅。如艾博齊塔和麥克唐納提到,“極右翼的幽靈之所以在歐洲徘徊,是因為它們巧妙地把歐洲一體化和全球化浪潮所引發的就業壓力、安全擔憂以及種族、文化危機,特别是身份認同的焦慮與民衆對代議制民主的不滿聯結起來,從而發動了一場又一場富有強烈極端化色彩的民主鬥争”。 ?
以2015年以來多起嚴重恐怖襲擊的發生地法國為例,極右翼勢力的主要政治旗号之一是“保衛傳統文化,排斥外來移民文化”。長期以來,法國都存在着不容小觑的極右翼排外勢力,國民陣線就是其中的重要代表,它集中了狂熱的民族主義、反對外來移民和敵視現有政治制度等特點。從成立之初,國民陣線就高度重視移民問題,創黨領袖讓·瑪麗·勒龐1978年在《世界報》發表了一篇題為“反對移民”的文章,稱國民陣線将成為“一個積極反對外來移民的政治組織”, ?其選舉活動都是以此為基礎。近年接連發生的恐怖襲擊則給了他們絕佳的擴大影響的機會。國民陣線現任黨魁馬琳娜·勒龐在《查理周刊》事件後頻出驚人言論,主張法國采取新的措施來應對迅速擴散的恐怖主義,包括切斷一些激進的寺廟和宗教協會的經濟來源,并對安全機構提供更多資金,甚至呼籲要恢複死刑。巴黎2015年11月13日發生多起恐襲之後,勒龐又稱:“法國和法國人已經不再安全,而我要告訴大家,我們必須采取緊急措施。法國應該分清敵我,一切與極端伊斯蘭勢力保持良好關系、與恐怖組織暧昧不清、與恐怖分子一道打擊我們盟友的人都是敵人。”她呼籲關閉受極端主義影響的清真寺,驅逐境内傳播反法思想的外國人,大力宣揚民族主義思想,煽動法國人的排外情緒。
近年來,在歐洲接連發生的恐怖襲擊引發了“伊斯蘭恐懼症”,很多極右政黨及極右翼分子利用恐怖襲擊給民衆帶來的恐慌,給穆斯林群體貼上危險、懶惰的标簽,認為其難以融入歐洲社會,應該限制和驅逐。正是不同群體在極端化中、思想層面上對彼此的認知偏見,使誤解和分歧難以彌合,沖突難以調解。就在《查理周刊》遭襲前一天,德國爆發了3萬人參加的“反對伊斯蘭化”遊行。慘案發生後短短幾天,法國發生了十幾起針對清真寺的襲擊。
這一系列的事件都是歐洲不同族群矛盾累積的表現。把極右翼政黨送入政府、參與極右翼政黨和極端組織發動的街頭暴力、發動瘋狂的個人報複社會等,成為部分普通大衆宣洩長久積累的不滿、憤怒和反抗情緒的渠道。下圖是貝倫貝格銀行2015年9月發布的一組調查數據,從支持率來看,歐洲很多國家的極右翼政黨都已經擁有了顯著的民衆支持度。?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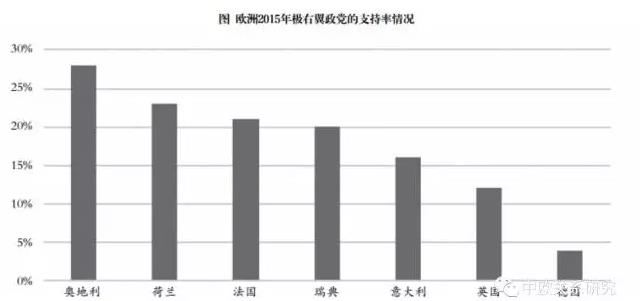
伴随極右翼政黨的崛起,是歐洲社會與民衆思想和情緒的極端化。20世紀50年代大批移民到歐洲成為勞動力,但由于文化差異、社會結構等問題,移民人口逐步發展為歐洲各國必須認真面對的難題,尤其是人數衆多的穆斯林移民群體,對所在國家的社會經濟和政治文化帶來了早先預料不到的巨大挑戰。弗裡施曾歸納歐洲移民沖突為:“我們召喚的是勞動力,但來的是人。”?進入二十一世紀,雖然排外主義的表現形式不如二十世紀那樣激烈,但歐洲很多國家依舊在經濟、文化、種族、血統和生活方式等方面,把外來移民看作是一種威脅。
有學者發現,群體之間的沖突,特别是伴随着持續暴力的群體沖突,會使得他們對彼此的消極認知變得越來越極端,極端到甚至把敵方非人格化。21例如,很多極右翼分子不承認穆斯林移民應該享有平等的居住權、工作權和社會福利,甚至許多穆斯林覺得“自己處于一種被懷疑參與恐怖活動的大環境中,像是二等公民”。22與之相應,穆斯林極端分子則認為歐洲的白人作為異教徒不配享有生命權。在極右翼政黨的動員下,很多歐洲民衆認為穆斯林社群無法接納西方價值觀,而且支持“伊斯蘭國”等恐怖組織。随着恐怖襲擊事件頻發,歐洲社會主流民衆與穆斯林移民之間的不信任感倍增,使得歐洲在族群關系上更為緊張。政府移民政策和媒體放大沖突的消極效應,也加深了少數族裔和主流社會之間的對立。
歐盟在2010年的一份報告指出:穆斯林群體通常在人口擁擠的貧民區居住,失業率高,例如法國穆斯林的失業率超過非穆斯林群體失業率的4倍。 23在移民融合過程中,對于移民影響最大的就是就業問題。在就業市場上,就業技能水平整體較低的有色種族移民本已處于弱勢地位,而政府和工會組織在政策上也采取放任和排斥的态度,因此有色種族的移民往往是最後被雇傭和最先被解聘的對象。移民在就業、教育、住房和福利等各方面經常遭受到不平等的對待,容易走向極端化。
歐洲不少媒體刻意的、有選擇性的片面報道,給穆斯林帶來了相當的負面影響。他們在報道中誇大穆斯林對當地社會的危害,例如失業率上升、犯罪率上升、增加财政和社會負擔等,煽動反穆斯林的情緒,而少有關于穆斯林曆史、文化的客觀報道。同時,歐洲媒體屢次對伊斯蘭教表示戲谑的态度。例如,2005年9月30日,丹麥報紙《日爾蘭郵報》刊登了一組12幅諷刺伊斯蘭教創始人穆罕默德的漫畫,引起伊斯蘭世界的強烈不滿。媒體這樣的報道不僅僅加劇了主流社會和穆斯林之間“我們”和“他們”之分,也潛移默化地傳達了“我們”必須要改造“他們”的信息。對于穆斯林群體來說,他們并沒有太多機會在主流媒體上發聲,媒體對穆斯林群體的一些帶有偏見的報道和消極評論加劇了穆斯林群體的社會邊緣化,無形中強化了他們對本群體的文化歸屬和身份認同,這為極端化創造了條件。
随着入境移民數量的增加,社會上的排斥心理也随之增強。以包容力強見稱的荷蘭,近年來亦對于不同種族和文化差異的移民表現出一種拒絕接納和要求對其進行同化的趨向。24從英國的一次民意調查可以發現,半數以上的被調查者認為應鼓勵白人移民,限制有色種族的移民,因為後者消耗了社會服務資源,帶來了疾病、肮髒不堪,引起就業競争。25
一些極右翼勢力也趁勢而動,2008年以來,歐州發生了上百起針對穆斯林移民的歧視暴力事件,包括暴力騷亂、沖擊清真寺和侮辱襲擊。2009年至2010年間,英國從法西斯組織英國國民黨( BNP) 在政治上的合法化,到如英格蘭防衛聯盟( EDL) 等草根階層抗議組織的誕生,極右力量從地下轉為公開。英格蘭防衛聯盟等極端分子從小規模、少數人以及缺乏組織的暴力犯罪,迅速發展為參與人數上千,組織嚴密、帶恐怖性質的經常性的抗議暴亂。2016年法國國家人權委員會的報告顯示,2015年法國境内反穆斯林犯罪事件達到429起,較2014年的133起激增了兩倍;而且仇恨恐吓或犯罪行為顯著增加約22%,達2034起。尤其在《查理周刊》恐怖襲擊事件發生後,針對穆斯林的犯罪案件達至高峰。26
德國的“愛國歐洲人反對歐洲伊斯蘭化”(簡稱“佩吉達”, Pegida) 是新近崛起的極右翼社會運動的代表。在《查理周刊》事件發生後,“佩吉達”呼籲在全歐洲範圍内進行抗議活動,在德國城市萊比錫,“佩吉達”的支持者與反對者嚴重對立,德國警方從全國調動四千名警察阻止雙方互鬥。目前,“佩吉達”的影響力已經超越國界,在比利時、奧地利、瑞士、瑞典和挪威等歐洲國家形成一定規模,也計劃組織與德國類似的反移民活動。在西班牙,右翼政黨民主國民黨的領導人曼紐爾·坎杜拉( Manuel Canduela) 在社交網站上聲援“佩吉達”号召實行“驅逐政策”,稱“歐洲是屬于歐洲人的”。27
2015年,德國接收了約110萬難民。大量難民的湧入導緻國内治安事件層出不窮,激發了主流德國民衆“向右走”的态勢,而老牌極右翼政黨德國國家民主黨( NPD) 也在多年的持續衰落後逐漸恢複了元氣。民調結果顯示,支持反移民政策的“德國選擇黨”支持率已升至近10%。28難民大規模湧入帶來了一系列社會問題,使得同情移民的主流民意迅速轉化為對德國難民政策的批評和對難民的恐懼,繼而開始向右翼極端化和保守化傾斜,而德國選擇黨、“佩吉達”和國家民主黨在一定程度上成為了排外、仇外民衆的精神寄托。
極化背景下的歐洲政治
在左翼激進化與右翼極端化的社會氛圍下,新崛起的小黨或邊緣性政黨嚴重地沖擊着傳統的政局,主流政黨左右遭受夾擊。首先,多國政府出現非正常政府更疊,政府難産導緻選舉頻繁發生,聯合政府成為新常态。2009年以來,歐盟内先後有意大利、希臘、西班牙、葡萄牙、愛爾蘭等近半國家發生政府更疊。希臘前總理帕潘德裡歐面臨國内外壓力黯然下台,意大利政壇不倒翁西爾維奧·貝盧斯科尼被迫辭職,具有小拿破侖之稱的法國總統尼古拉·薩科齊壯志未酬,痛失2012年蟬聯總統的機會。從2009年到2015年希臘因組建政府困難而先後舉行四次選舉,最終左翼激進聯盟脫穎而出。2015年12月與2016年6月,西班牙連續舉行兩次選舉,因無一政黨獲得議會多數,直到10月底才勉強組建一屆脆弱政府,出現了長達10個多月的無政府局面,新崛起的左翼選舉聯盟“我們能”位居第三,對傳統政黨格局造成嚴重沖擊。2010年6月~2011年12月,比利時大選後因北部荷蘭語政黨與南部法語政黨無法就國家政體改革達成一緻,新一屆聯邦政府遲遲未能成立,創造了541天無正式政府的世界紀錄。
其次,在激進左翼與極端右翼的沖擊下,一些主流政黨被迫向兩極靠攏。出于政黨競争的需要,主流政黨在選舉的壓力下效仿激進極端政黨的某些主張。最典型的例子是,由于極右翼政黨對移民政策的嚴苛态度使其輕易赢得部分選票,于是,有些傳統中左派政黨為了讨好選民也開始在移民問題上右傾化。2013年,法國社會黨政府驅逐羅姆女孩,引發巴黎及全國各地的移民少數族裔青少年的示威遊行。總理瓦爾斯則對此表示:“我們應為我們所做的感到自豪,而不是感到抱歉”。強硬程度與上屆中右翼政府并無二緻。與此同時,中右的人民運動聯盟黨也在變得更右。2013年10月,人民運動聯盟黨主席科佩( JeanFranois Copé) 提出,法國移民政策應該變更,從法國大革命以來實行的屬地原則改為血統原則。這一提議實際上是極右翼政黨20多年來一直主張的。29在2017年的總統選舉中,主流右翼候選人的政策保守化趨勢日漸突顯。争奪總統寶座最具競争力的法國右翼共和黨候選人弗朗索瓦·菲永,不僅在經濟上采取撒切爾式的新自由主義路線,而且在國家建構和移民融合問題上采取了與極右翼政黨國民陣線相似的政策主張,對移民與伊斯蘭持強硬立場;菲永在電視辯論中公開稱法國“并非一個多元文化國家”,那些來到法國的外國人必須尊重法國的社會風俗。在對歐問題上,菲永雖主張留在歐盟,但強調前提是能夠維護法國的利益,在對外政策上趨于保護主義。
2016年12月,德國基督民主聯盟再度選出安吉拉·默克爾為主席參加2017年總理競選。默克爾一改之前在移民問題上接納、包容、開放的态度,在黨代會上表示德國應禁止罩袍,德國法律優于伊斯蘭法,2015年難民潮不應也不會再重演,等等。值得警惕的是,歐洲的這種極端社會情緒正在醞釀産生新的基層極端政治組織。例如,在2016年3月和9月,德國執政黨基民盟和社民黨在聯邦議會選舉和柏林地方選舉中遭重挫,相反,兩次選舉中均看到極右翼政黨“德國另類選擇黨”的崛起,該黨在9月選舉後首度進入柏林市議會,甚至還獲得德國16個聯邦州中的10個州的議會議席。同時,在“佩吉達運動”中,有不少極右翼黨派“德國國家民主黨”的成員,這些成員試圖通過排斥穆斯林等方式來獲得極端保守主義者以及新納粹分子的政治支持,為其在将來的德國議會選舉中積累更多的政治能量和籌碼。
2015年5月英國大選,主張脫離歐盟、限制移民的獨立黨首次取得國會議席,成為2016年英國脫歐公投中的中堅力量。英國前首相卡梅隆政府之所以以自己的政治生命做賭注舉行脫歐公投,主要壓力是來自英國獨立黨崛起的選舉競争。脫歐公投後的英國保守黨新領導人特蕾莎·梅則完全接過民粹主義的大棒,不僅在移民問題态度強硬,而且還禁止非英國公民參與英國脫歐問題的讨論和設計。與此同時,自從工黨下野以後,黨内精英與草根的矛盾也日漸突顯,草根代表傑裡米·科爾賓憑借普通階層的支持,以絕對優勢當選工黨黨魁,黨内政策急劇左傾。科爾賓被稱為工黨内“堅定的社會主義者”,他反對布萊爾時期第三條道路,主張把重要的壟斷行業和公共服務領域重新國有化。英國脫歐公投後,科爾賓的黨内權威面臨空前挑戰,但他仍憑借“草根”優勢連任黨魁,挫敗黨内精英“政變”,繼續執行激進的左翼政策。不僅如此,具有地方主義色彩的蘇格蘭民族黨在經曆蘇格蘭獨立公投及脫歐公投後力量大增,其政策比工黨和自由民主黨更左傾,更激進。
總之,面對激進左翼與極端右翼政黨的夾擊,主流政黨已陷入困境,為赢得選舉,被迫在不同程度上内化和吸收反建制政治力量得以獲得選票的主張和政策。因此,在可見的将來,整個歐洲政治的趨勢将繼續呈現出民粹化的局面,主流政黨推進歐盟一體化的動力将有所減弱。2017年,法國和德國迎來大選,有可能成為法國總統的菲永和德國總理的默克爾雖然不會挑戰歐盟的整體性,依舊主張留在歐盟,但在反歐主義興起的壓力下,會更強調國家利益優先。歐盟成員國的非主流激進或極端政黨力量的上升及民意的民粹化将進一步沖擊歐盟作為超國家政治經濟組織所擁有的權力和作為後民族共同體所構建的價值觀念。激進或極端政黨反對歐盟對民族國家事務的管控權和決定權,激進左翼主要反對歐盟在貨币和财政緊縮問題上的政策,極端右翼主要反對歐盟在移民問題上的邊境開放、難民安置等安排。同時,面對國内的移民少數族裔尤其是穆斯林移民,極端右翼的主張也較多反伊斯蘭和排外主義的色彩;這些主張與歐盟的人員自由流動、尊重并促進文化多樣性的價值理念背道而馳。在未來一段時間内,歐洲政治與社會的激進化與極端化方興未艾,會極大沖擊歐盟作為超國家共同體的政治權力和價值理念,削弱歐盟建構共同體的意識形态基礎。
歐洲政治與社會的極化現象具有錯綜複雜的曆史和現實原因。從曆史上,全球化、歐洲一體化一直鼓勵的文化多元化推動了歐洲經濟與社會的成功發展,但長期以來也累積了一些負面問題。全球化強調人員、勞動力及資本的自由流動,有利于各民族之間交往、溝通和融合,但它也同時打破了過去各民族地區分散、孤立的狀态,加大了民族矛盾暴露與激化的機率,拉大了經濟發展不平衡和貧富差距,削弱社會團結一緻的基礎,創造了反對民主原則本身的身份認同、價值和欲望等,對政府的正常運行和社會凝聚提出了巨大的挑戰。從現實看,伴随着歐洲債務主權危機及大規模的中東和北非難民潮的湧入,歐洲内部各種政治與社會情緒發酵。國家債務危機與歐盟開出的财政緊縮條件加重了成員國與歐盟之間的緊張關系,而歐盟與成員國之間就緩解歐債危機和難民危機的拉鋸戰進一步凸顯了歐盟“民主赤字”的問題。歐洲民衆在頹喪感的作用下,對當前的執政黨和歐盟高度市場化産生強烈不滿,持激進左翼思想的民衆通過遊行示威以及支持激進政黨來幹預政府的政策制定,由此催生出南歐諸國的左翼民粹主義及激進左翼情緒。經濟下滑在福利、就業、安全等方面的影響,以及恐怖組織“伊斯蘭國”的壯大,加劇了歐洲中下層民衆對穆斯林難民的排斥和對國内融入困難的移民的歧視,國家民族主義者急于打破“政治正确”,不滿于當下的建制,由此催生出右翼民粹主義。這樣,主流政黨不時地處于左右夾擊之中,在社會氛圍整體趨于保守或右傾的趨勢下,更多的主流政黨政策右傾化更趨明顯。
近年來歐洲疊加的矛盾是多年來全球化及歐洲一體化積累而成,全球及歐洲主流政治解決問題的能力決定了極化背景下激進化與極端化的力量能走多遠。從未來趨勢看,全球性危機仍在加劇着社會不安情緒;主流政黨解決問題乏力使得各種左右翼極端政黨将問題單一化的解決途徑受到選民追捧;新媒體追求刺激和吸引眼球式的誇張言論更是為各種極端力量推波助瀾。這些因素導緻了各種激進或極端政治思潮在短期内不但不會偃旗息鼓,而且會在更大程度上與主流政治分享權力,這将增加歐盟一體化之艱難,增加了歐洲政治的不确定性,弱化歐洲的整體力量及其在世界政治中的地位。這不僅是歐洲的問題,更是世界上許多國家共同面對的緊迫難題,需要認真思考。
(本文是外交部課題“當前歐洲政治激進化及其對歐盟對外政策影響研究”的成果之一,也是2016年度教育部人文社會科學重點研究基地重大項目“歐美主要國家執政黨治國理政經驗教訓研究”的階段性成果,項目編号為16JJD710009;同時感謝beat365國際關系學系碩士研究生劉浩在文章前期收集資料以及起草過程中發揮的重要作用)
注釋:
①在歐洲和國際政治界以及國内國際學術界中,關于歐洲模式這個名詞早有提出,涉及經濟、社會、政治和安全,以至福利、文化等方面。大體上以和平、穩定、團結和社會經濟均衡發展為目标,在多元一體和主權共享的原則指導下,遵循共同的法規、在共同的體制機制下實行以國家和區域兩個層級為主的相互協調多層互動的區域共同治理,同時受價值觀指導、帶意識形态色彩,甚至夾雜着意識形态偏見和利己主義思考,使用各種手段強制推行其價值觀和規制秩序,還存有“歐洲中心論”和“歐洲文明優越論”的影響。
②PaulDiMaggio, John Evans and Bethany Bryson, "Have American Attitudes Becomemore Polarized ? " American Journal of Sociology, Vol.102, No. 3 (Nov.,1996), p. 693.
③[英]戴維·米勒、韋農·波格丹諾:《布萊克維爾政治學百科全書》,鄧正來等譯,北京:中國政法大學出版社,2011年,第469頁。
④BritishGovernment, Prevent Strategy, June 2011, p.107.
⑤HomelandSecurity Institute, Radicalization: An Overview and Annotated Bibliography ofOpenSource Literature, Arlington: HIS, 2006, pp.2-12.
⑥Ministryof the Interior and Kingdom Relations, "From Dawa to Jihad: The VariousThreats from Radical Islam to the Democratic Legal Order," The Hague:General Intelligence and Security Service, 2004, pp.13-14.
⑦[英]霍恩比:《牛津高階英漢雙解詞典》,石孝殊等譯,北京:商務印書館, 2005年版,第1416頁。
⑧AlexP. Schmid, "Radicalisation, DeRadicalisation, Counter-Radicalisation: AConceptual Discussion and Literature Review," ICCT research paper, March2013.
⑨李週:《從金融危機中法共主張看共産主義運動可持續發展》,《中國社會科學報》,2011年10月8日。
⑩https://npa2009.org/node/38455.
?希臘激進左翼聯盟發起的“拒付款”運動,反對高速公路收費。
?LorenzoViviani, The New Left in the European Democracies: The Case of the GermanRadical Left, Free University of Berlin, 2013.
?意大利五星運動一度被界定為左翼,但自2014年6月與英國獨立黨聯合在歐洲議會中組成新的黨團——歐洲自由民主黨團後開始被界定為右翼。五星運動有5個核心主張,即水資源公有、反高速鐵路、發展、環保和直接民主。在2016年12月反對倫齊總理的憲法公投中,五星運動是核心的組織者。
?史志欽、劉力達:《民族主義、政治危機與選民分野——2014年歐洲議會選舉中極右翼政黨的崛起》,《當代世界與社會主義》, 2015年第2期,第113~114頁。
?自2010年議會選舉後,匈牙利國會規模從386席削減為199席。
?Givens,Terri E., Voting radical right in Western Europe, Cambridge University Press,2005, pp.139-149.
?DanieleAlbertazzi and Duncan Mcdonnell, Twenty-first Century Populism: The Spectre ofWestern European Democracy, Palgrave Macmillan, 2008.
?HarveyG. Simmons, The French National Front: The Extremist Challenge to Democracy,San Francisco: Westview, 1996, p.79.
?http://www.businessinsider.com/europeannationalism-risk-2015-9.
?Aspeech made by Max Frisch on the topic of immigration at a Swiss Border patrolpolice station in Lucerne, first published in the Swiss newspaper Die Weltwocheon September 9, 1966.
21Donatella della Porta, Social Movements, Political Violence, and theState: A Comparative Analysis of Italy and Germany , Cambridge UniversityPress, 1995, pp. 173-174..
22羅愛玲:《存在與沖突——試論穆斯林移民對歐洲政治與社會的影響》,《世界民族》,2009年第3期。
23Susan McVie and Susan Wiltshire, "Experience of Discrimination,Social Marginalisation and Violence: A Comparative Study of Muslim andNon-Muslim Youth in Three EU Member States", European Union Agency forFundamental Rights, December 2014.
24Maykel Verkuyten and Ali Aslan Yildiz, "National (Dis)identification and Ethnic and Religious Identity: A Study among Turkish-DutchMuslims", Personality and Social Psychology Bulletin, Vol.33, No.10, 2007,p.1446.
25Power, Jonathan, Migrant Workers in Western Europe and the UnitedStates, Pergamon, pp45-46.
26新加坡《聯合早報》, 2016年5月4日。
27http://www.oushinet.com/news/europe/eu/20150115/179379.html.
28觀察者網:《科隆性侵案引發民衆恐慌德國右翼勢力趁機發展壯大》,2016年1月8日,http://www.guancha.cn/europe/2016_01_08_347383_1.shtml。
29劉力達:《驅逐羅姆女孩:法國政治的右轉與歐盟幹預效力的弱化》,《中國民族報》,2013年11月8日。 Reinhard Heinisch, "Success in Opposition-failure inGovernment: Explaining the Performance of Right-wing Populist Parties in PublicOffice", West European Politics, Vol.126, No.3, 2003, pp.103-109。
文章來源:《人民論壇·學術前沿》,2017年第3期。
